- ###课程目录:周之江·安神晚课## 发刊词(1讲)发刊词|365个夜晚,我在花溪河畔跟你道晚安## 2023年2月(15讲)02.14|当爱情以另外一种方式铺展02.15|回到故乡,物是人非也不怕02.16|不能说走就走,就去读游记吧02.17|幸好人生还有“乌云的金边”02.18|食物才是乡愁的解药02.19|所谓疗愈,无非是“放下”与“放过”02.20|在大庭广众之下读《性心理学》02.21|出手那么酷,爱得又那么暖02.22|鸡毛蒜皮的武士也动人02.23|藤泽的武士和金庸的侠客各有各的难处02.24|所谓猫债,也是情债02.25|和另一半吃不到一块怎么办?02.26|天宫亦职场,神仙打工人02.27|如果苏东坡没有粉丝的狂热02.28|晚间请你听一个探险故事## 2023年3月(31讲)03.01|猎人的归宿是森林03.02|“黑暗森林”首先是在地球上03.03|被鲁迅痛骂的也不一定是坏人03.04|在家请客总是胜过下馆子03.05|“复制品”里一样有工匠精神03.06|能讲故事的时候就不要讲道理03.07|“路怒症”也可能是一种时代病03.08|“世界的尽头”还有一位了不起的女性03.09|跟孩子一起读《丁丁历险记》吧03.10|一个中国人对丁丁影响至深03.11|最好的下酒菜是一碟花生米03.12|每天记日记,就有史料价值03.13|有妖气的蓝兔子,创造性的调皮03.14|爱情在文字里永生03.15|黑泽明都被自己吓出一身油来03.16|世间何事不昙花03.17|怦然心动,最是人情03.18|辣到痛处成痛快03.19|当“地图炮”遇到哲学家03.20|我们总是禁不住追问历史03.21|小丑才是那个聪明人03.22|存疑,但别被阴谋论绑架03.23|记录下来,别等消失了再遗憾03.24|堵在路上脑洞大开03.25|在一杯新茶里喝到春天03.26|给书穿一件衣服就安心了03.27|《夏洛的网》,用爱织网03.28|“诗和远方”在城市也在农场03.29|“街道江湖”上的凡人悲欢03.30|大哲学家也是办事高手03.31|陈凯歌去当导演是作家的幸运## 2023年4月(30讲)04.01|贵阳人发明了“湖南面”04.02|盖棺而已,尚未论定04.03|中国式的应酬并不是应付04.04|像人类学家那样保持天真04.05|清明:看花也不会耽搁赶路04.06|“老北漂”齐白石的乡愁和亲情04.07|那些让我们捶胸顿足的失落之书04.08|把美食从书本搬上餐桌04.09|时代曲的密码是土洋结合04.10|能逗笑我们的都是普通人04.11|在别人的自传里了解王小波04.12|金石难灭,托以高山04.13|猜一猜沉默石头的心事04.14|懂一点麻将又如何?04.15|烧烤密码:深夜、烟火和老友04.16|北野武和他的“虎妈”04.17|韦小宝其实是个流浪汉04.18|好肖像不光有脸,更有故事04.19|当面打瞌睡胜过背后捅刀子04.20|聪明的一休也是疯狂的一休04.21|从“E考据”到“A考据”04.22|梦到吃不到,最是意难平04.23|有必读书目,就有不必读书目04.24|居一地,也应该爱一地04.25|被收藏家坑了的王羲之04.26|身世扑朔迷离的《兰亭序》04.27|推理一桩《兰亭序》的造假悬案04.28|苦也珠崖,乐也珠崖04.29|宫保鸡丁何必原教旨主义04.30|小说多佳偶,柴米生怨偶## 2023年5月(31讲)05.01|百年前的中国“十八省府”05.02|西泠印社:文人抱团做成了百年老店05.03|文明是交流灌溉出的奇葩05.04|文明与野蛮,五十步笑百步05.05|挠到痒处,才算得上如意痛快05.06|家人围坐的晚饭时光不容打扰05.07|古琴有雅意,故事亦安神05.08|螺丝钉竟然是千年最佳工具05.09|道不同也可以相为谋05.10|有心的话无聊也能变有趣05.11|张爱玲和钱锺书的“被发现”05.12|从“易先生”到真实的丁默邨05.13|“油腻中年”,素食可解05.14|食素吃肉,各自表述05.15|黯然销魂者,惟桥而已矣05.16|窃书,终究还是偷05.17|摩登上海的前尘小事05.18|悲欣交集缘缘堂05.19|梁左:喜剧天才,人间清醒05.20|为折耳根“折腰”05.21|给小红帽的童话来个“煞风景”解析05.22|老舍写职场也入木三分05.23|手工纸可不是宣纸这么简单05.24|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”也是个本事05.25|当绘本大师遇到真正的教育家05.26|求神问卜,不如问问自己05.27|肥而美的,唯有红烧肉05.28|健康的人生要兼容一点不健康05.29|过尽千帆,还能超脱释然05.30|鬼故事只能讲到第九十九个05.31|我们喜欢会讲笑话的人## 2023年6月(30讲)06.01|保留一点孩子气06.02|从唱别人的歌到唱自己的歌06.03|初夏,别错过杨梅滋味06.04|真正的好文笔都是细节控06.05|在街头巷尾找到学问的用武之地06.06|不雅之物也可以一本正经地聊06.07|为中国人画像的晚清外交官06.08|无论低谷高潮,难得百折不挠06.09|把“腌萝卜”当作旅行主题06.10|萝卜的妙处在于乡土本色06.11|成年人依然可以相信“童话”06.12|从街头俗书到艺术殿堂06.13|终归回不去的童年与故乡06.14|百年连环画的辉煌与落寞06.15|我看人看我 倩女可离魂06.16|一个母题开出千姿百态的花朵06.17|粽子何妨南北一家亲06.18|在李安的“父亲三部曲”里照见自己06.19|没大没小没“爹味”06.20|在365天复刻524道菜中走出困局06.21|能写好菜谱的真不是一般人06.22|送礼:中国式的人情往来06.23|读闲书不如“闲”读书06.24|“苍蝇馆子”乐趣多06.25|关于胡子的“胡说”06.26|谁还没有个“一地鸡毛”?06.27|俞平伯和几个老朋友06.28|有趣且有用的经济学观察06.29|诗人陆游的不同侧面06.30|一场游戏一场美梦## 2023年7月(31讲)07.01|天生荔枝难自弃07.02|肉身凡胎,谁能不生病07.03|一扇清凉的善意07.04|怪力乱神说不得,画得07.05|名为片子,实为面子07.06|藏书票里藏世界07.07|我把远方的远归还梦田07.08|外来的番薯劳苦功高07.09|老子与孔子谁更老07.10|香和臭,不仅仅是嗅觉感受而已07.11|张恨水:小说家对《水浒》的同行评议07.12|马幼垣:学者唱反调的《水浒》人物评点07.13|摆一个绝妙宋茶的“龙门阵”07.14|人生往事,在书页里留痕07.15|带你来一趟贵州吃酸之旅07.16|樊建川:收藏历史的边角废料07.17|一本口述自传的口述实录07.18|回忆也不都靠得住07.19|不满意是进步的动力所在07.20|从胡床到椅子:坐姿改变生活07.21|是“救赎”之道,也是希望之春07.22|天生重口味,盘中“肠相思”07.23|亲亲呀我的宝贝07.24|《周作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》为何堪称“三绝”07.25|三个各有各精彩的大女主07.26|带刺的诗人汪曾祺07.27|暖哉汪曾祺 人间送小温07.28|醉酒:在理性与感性之间07.29|高阳酒徒聊茅台07.30|大出版家跟他的明星作者07.31|自称学徒的中国出版人## 2023年8月(31讲)08.01|世间心病 小说包治08.02|雷峰塔下有真经08.03|草蛇灰线《白蛇传》08.04|《封神演义》是古典小说版的“王者荣耀”?08.05|红尘匹马长安道08.06|藏书印里名堂多08.07|战火纷飞下的“读书会”08.08|一只蝉的复杂切面08.09|《罗刹海市》的追根溯源08.10|漫漫长夜孤灯独守的郑振铎08.11|鼻子是鼻子,执念归执念08.12|西瓜不妨改名叫“夏瓜”08.13|姓名有禁忌 性命相关连08.14|《春江花月夜》的逆袭与上位08.15|“金子”一样美丽的童谣诗人08.16|诗人也能像水浒英雄一样排座次08.17|菜单、食物名背后隐藏的秘密08.18|一个谐音梗,油炸秦桧几百年08.19|天下油炸是一家08.20|苏州园林的守护者08.21|一块古碑引发的少林“悬案”08.22|毛姆如何看待婚姻?08.23|芥川龙之介眼中的中国08.24|大导演李翰祥的电影人生08.25|乐队的夏天:综艺里的“海盗电台”08.26|云南野生菌的魔力08.27|饭局:《读书》杂志的“经营”之道08.28|金农的文人画,究竟好在哪儿?08.29|中国人的“吸猫”史08.30|毛姆:要财富还是要自由?08.31|米芾、倪瓒也“洁癖”?## 2023年9月(30讲)09.01|就算打喷嚏,也会有“禁忌”09.02|重庆火锅是我们的共同“损友”09.03|李碧华的神秘与才情09.04|“宋体字”为何脱颖而出?09.05|如何给学术大师排江湖地位?09.06|契诃夫的文学札记09.07|一个脑洞:如果金庸是武术史家09.08|给《西游记》打一个梦的“补丁”09.09|来一碗中国式“果冻”回忆杀09.10|不该被遗忘的两位“乡村教师”09.11|十一枚戒指背后的NBA夺冠秘诀09.12|“禅师”杰克逊的东方智慧09.13|《长安三万里》为啥有那么多离别诗09.14|“封神榜”为何敌我不分?09.15|哪吒和《封神演义》的前世今生09.16|新米滋味就像人生况味09.17|写错别字的一流诗僧八指头陀09.18|“凡事认真”的弘一法师09.19|《民间情歌》:味道纯正的“土味情话”09.20|《王能好》:悲剧底色的喜剧人09.21|要想不太“倦”,就得不太“卷”09.22|钱锺书的“个人向”唐诗选本09.23|馋的就是这一口焦香的锅巴09.24|《阴阳师》:“咒”是人心和人性的映射09.25|日本的“阴阳师”究竟是怎样一类人?09.26|从小说译名,看中西文化差异09.27|鲁迅也是“颜值控”09.28|乐队的夏天:一首《大梦》凭什么出圈09.29|中秋吃月饼有个刀光剑影的传说09.30|月饼一块寄相思,哪怕只吃一小块## 2023年10月(31讲)10.01|中国古人能有多幽默10.02|前人文字里的北京之秋10.03|面包、啤酒是怎么传入中国的?10.04|明代的“反诈骗”读本长啥样?10.05|像电影分镜头脚本一样的漫画10.06|一对伟大艺术家的以“舞”结缘10.07|娇贵妖娆如精灵的竹荪10.08|漫画里的“三毛”也能登上文学殿堂10.09|从课堂笔记感受顾随的“讲课艺术”10.10|心中有诗意,人生大境界10.11|蒙古“马头琴”话说从头10.12|“磁版印刷”为何昙花一现?10.13|鲁迅为何难免盛名之下的沉重10.14|包子包子,当然可以无所不包10.15|武则天“无字碑”也许是“无字天书”10.16|任伯年:晚清人物画的第一流高手10.17|徐悲鸿为啥成了任伯年的“小迷弟”10.18|如何名正言顺地读名人“八卦”10.19|除了做攻略,建议你写写旅行日记10.20|黄酒才是中国古代的主流存在10.21|吃过大闸蟹,才算是不辜负秋色10.22|侦探小说都有哪些常规套路10.23|借一本小说诠释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10.24|抄书,抄到什么程度算是“抄”10.25|一个设计师的“吐槽”与坚持10.26|中国古人为啥爱在墙壁上题诗10.27|《救荒本草》:教“草根”如何识草根10.28|吃野菜,吃的就是一口野趣10.29|林青霞算不算是一个好作家10.30|叶灵凤和他的后辈知己李广宇10.31|都是爱书人,悲欢皆相通## 2023年11月(30讲)11.01|李白、崔颢真为黄鹤楼斗过诗吗?11.02|两情若是相悦时,朝朝暮暮更好11.03|《美食家》:何止是美食回味无穷11.04|别把吃饭变成了吃碟子、吃杯子11.05|一个老北京人的东四二条十年回忆11.06|为什么说“人情世故”也是大学问11.07|启功:是书法大师也是“幽默大师”11.08|特别普通的“小人物日记”11.09|一百多年前的北京风俗画11.10|“碗”为什么能够晚来居上11.11|奇妙滋味数豆豉11.12|是段子,也是艺术史的有趣片段11.13|两百多年前的朝鲜文人如何看中国11.14|“小抄”文章里有大思考11.15|青灯红烛,也浪漫也麻烦11.16|一本观鸟日志,两颗心灵相通11.17|齐白石为啥以“草间偷活”的虫子自喻11.18|大白菜为何成为“菜中王”11.19|谷村新司:星光灿烂的一生11.20|“师生情”何以动人至深11.21|“二手书”里里外外故事多11.22|“技击”故事背后的民族危机感11.23|借,还是不借,这是个难题11.24|犯了错为何总是屁股遭殃11.25|贵州“糟辣椒”可以捧一切11.26|既不威尼斯也不日记的《威尼斯日记》11.27|杨绛“保姆三部曲”里的悲喜人生11.28|为《北京风俗》图册题词的姚茫父11.29|泰戈尔没写过的五言古体诗11.30|儿歌不必有意义,但必须有意思## 2023年12月(31讲)12.01|为什么说《水浒传》是部“众创”小说12.02|港式奶茶:又土又洋平民味12.03|网络社交时代的珍珠、奶和茶12.04|一位“老北大”絮絮叨叨说往事12.05|《杨柳风》:冬天的炉边之书12.06|“吹牛拍马”是打哪来的?12.07|“抛绣球”:是真民俗还是编故事12.08|金圣叹为什么要“腰斩”《水浒传》12.09|为什么说贵阳才是真正的“火锅之城”12.10|鼎:是高级礼器,更是吃饭家伙12.11|张中行笔下的人、事、情12.12|烂柯山传说为啥是个大杂烩12.13|一个清代文人的低级趣味12.14|“三余”和“三上” 算笔读书账12.15|《教坊记》里的唐代娱乐圈往事12.16|“一品锅”的大杂烩里有学问12.17|如何看待食物的禁忌与疗、养12.18|林海音女婿的寻父之旅12.19|文人画家:汪曾祺的另一面12.20|《遍地风流》里的“青春残酷物语”12.21|为什么不能得罪食堂大师傅12.22|乔峰郭靖互为镜像为哪般12.23|冬至怎能不吃羊肉进补12.24|冬藏夏取:中国古人的用冰之法12.25|圣诞本无树,原是“摇钱树”12.26|“百苗图”:贵州少数民族众生相12.27|包罗万象的“百苗图”12.28|成都咋会有块织女“支机石”12.29|知识女性视角下的“平成时代”12.30|捏成一坨的黔中古风“糯米饭”12.31|到底该“上扬州”还是“下扬州”## 2024年1月(31讲)01.01|哪有先生不说话,每次发言都重要01.02|关于汪曾祺的1000件事01.03|别让恶俗书法砸了招牌01.04|“毒舌美人”:戏谑背后有洞见01.05|一天几顿饭才是古今常态01.06|集火锅、烧烤之长的贵州烙锅01.07|国之重器,如何完“鼓”归“京”01.08|“谜一样的男子”金圣叹01.09|圣叹只留书种在,才子狂生兼怪杰01.10|讲究“因循”的古代岁时风俗01.11|“绿遍池塘草”里有情深无限01.12|《东坡题跋》为啥是本“枕边书”01.13|丝娃娃的“丝丝”记忆都在牙巴上01.14|不好笑的笑话,才是个笑话01.15|归去来兮《黄州寒食帖》01.16|去今未远的八十年代事与物01.17|打牙凿齿的习俗是咋来的?01.18|为什么说宋江身上有岳飞的影子?01.19|“老派少女”走的什么购物路线?01.20|豆花:硬是把豆腐吃出了花01.21|“香港脚”的锅,不该让香港来背01.22|不是戏曲迷,但可以迷戏曲画01.23|《闪亮的日子》也是黄金岁月01.24|桃符到春联,辟邪变祈福01.25|春联也得“贴着人物写”01.26|“晚课”留言把这门课给讲“厚”了01.27|蘸水里边名堂多01.28|弘一法师的“孩童体”书法该怎么理解?01.29|上海:“繁花”之外,还有茂叶01.30|毛笔如何从“有心”到“无心”01.31|毛笔的“毛”都是些什么材质?## 2024年2月(13讲)02.01|《围城》跟毛姆有什么奇妙渊源?02.02|诗人流沙河如何接地气地讲《诗经》?02.03|名副其实的“民生”网红街02.04|“得到”老师分别对应哪些《水浒》人物?02.05|“古城”大理有古风02.06|启功题跋:妙趣横生有干货02.07|书画鉴定为什么要“留有余地”?02.08|“晚课”和留言,都像是窗口02.09|李伯清:西南人民的“喜剧之神”02.10|年夜饭:馋那一口“家的味道”02.11|方言为啥子更喜感、更出彩?02.12|蔡澜:会是“晚课”同学的“菜”02.13|让我们回到开始时的那家书店
微信扫一扫添加

朋友圈福利每日更新
微信号
dzzscb
© 版权声明
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,未经允许请勿转载。
THE EN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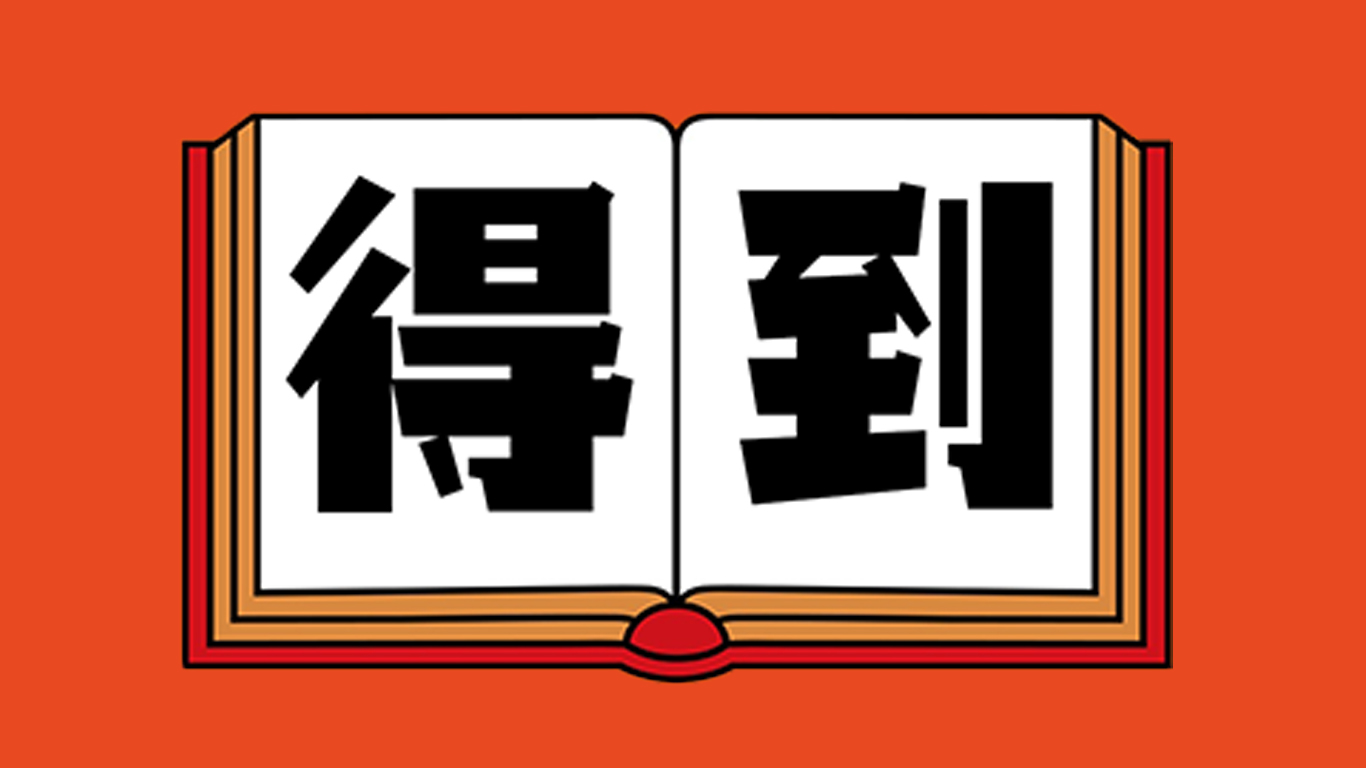

-趣学古诗词【视频课】.jpeg)


暂无评论内容